“举子业”的成本
——一个明代学子考科举到底有多花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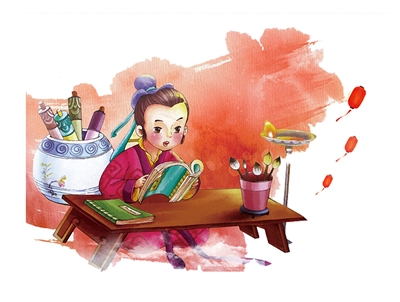 |
■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常权
在古代,寒门子弟考功名又被称为“从举子业”,这就很形象了,这简直就是明白地告诉大家,读书考科举,说白了就是一门生意。不过从读书人的角度出发,冠冕一点地说,科举制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通过才能对文人进行选拔考核,让他们成为朝廷的官员,为国效力。
想到科举制的考试方式和考试目的,我们对照现实很自然地便会想到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也是十年寒窗苦读,也是通过才能考试去为国效力。我们现在也知道一个人要备战高考或是公务员考试的花费颇多,在古代考科举是不是也要花上很多钱呢?
虽然科举考试改变了以前靠出身门第选官的局面,但是光有才能也是不行的,无论是备考还是赶考,都是需要钱的。那么我们就看看一个人想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究竟需要有多少科举花费支出呢?由于本文的主要参考数据都来自刘明鑫博士的专著《明代科举考试费用及其影响研究》,因此文章就以明代学子考科举为例。
备考的各项开销
在备考时的开销主要是在聘请老师和各种书籍文具上。
首先是聘请老师。科举考试分三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第一场的经义,经义之文便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八股文,也即时文制义。时文制义比较讲求答题技巧,以实用盛行于世。为了增加中举的可能性,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在平时学校学习外,纷纷延请精于作文技法的名师对其子弟进行单独辅导。
如朱国祯《涌幢小品》便说“自制义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为师友教子弟,即圣人复起,亦不可废”。在时文制义盛行于世的背景下,经济富裕的家庭聘请名士辅导子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明初,一些士子的延师费是以实物的方式支付。正统年间,白良辅“请业河东薛瑄”便是以“十艇肉为贽”的。这个时候聘请老师进行指导的花销并不多。
明中叶以后,随着货币经济的日益发展,白银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币,考生的延师费也逐渐以白银货币的方式支付。其具体费用又因经师名气、声望、才学等文化资本以及士子家庭经济实力等硬性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以江南为例,少者,每月开支数两,更有甚者不到1两。冯时可的《雨航杂录》便提到:“有谢简者,字一默,先君延为馆师,诲余兄弟三人,岁馈米三十斛”;多者每月开支为20~40余两。万历十八年,应天府开府少司马赵可怀便“命一承舍具聘书,每年具修脯二百四十金,别具彩缎二、银花二,令本地府县等门延请”著名经师庄廷臣,并让其教导自己的两个孩子;更有甚者,不是按年、月来聘请老师,而是按篇计价。在顾炎武的《日知录》便提到“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
聘请老师单独辅导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会选择的,其价格也各有高低。此外,还有平日于书院学校里学习的各种开销。
其次是准备书籍文具。像我们现在准备各种考试也需要教材一样,书籍是明代士子重要的复习与备考资料,图书费在有的考生的备考费用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像是费宏便“肆力于学,居常茹淡服素,节缩经费为购书资,淹通载籍,自为一家言”,后来便考上了进士,还是廷试第一人。根据魏大中的《藏密斋集》可以知道,他通过教书拿到了十金,“先孺人岁可费六七金,余金则买书读之”,可见魏大中备考的图书费为3-4两。
还有一些士子由于家境贫寒,只能以借书或抄书的方式来复习备考。像是黄钺“少明敏好学,家无藏书,钺日游市肆中,见书,不问古今,即借观之,或竟日不还”,后于考中了进士。又有人名冯友,“家贫不能购书,手写诵读,日夜不少休,时已知种学绩业,崭崭自树矣,弱冠游胶庠,每试輙诎其曹”,后来他考上了乡试。
除了考试用的书籍教材外,笔墨纸砚等文具也是备考和考试时的所需。单就考试时所要用到的文具而言,明承元制,规定试卷、笔、墨等考场文具需要由考生自备。晚明小说《欢喜冤家》中有所反映,扬州府仪真县秀才许玄开出了一张购置进场之物的账单:“自买卷子、文房四宝,一应进场之物,共要十两银子。”
可以看到,单单在考试时的文具花费就需要10两,更不用说平时所需要的了。考生除了需要购置试卷、笔、墨、砚等必备文具外,还需要购置考篮、烛台、卷袋、书箱等其他考试用具,这又是一笔花销。
赶考的各项开销
备考得差不多了,十年磨一剑,那自然要去考场上检验自己了。这前往考场的路费、住宿费和伙食费又是许多的开销。
交通费用。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需从居住地赶往考试地,自然产生相应的交通费用。明代科举又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考试五级考试构成,无论是参加科考、乡试,还是参加会试,交通开支皆是每位考生必须支付的一笔费用。
我们以会试为例,考生参加会试则由居住地赶往京师,属省际之间的流动,大部分考生的路程更远,时间更多,旅途亦更加艰辛,故其交通费用在各个时期也比科考和乡试高。
明初,会试生交通费用大致不超过10两。根据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郑真的《荥阳外史集》中所记载,他启程会试北上,用了1个月零11天抵达京师,他和仆人两人赴考期间的路费“用千余文”。
明中叶以后,会试考生交通费用逐渐升高,达到数十两甚至100两。越是离考试地更偏远的地区或是路途崎岖的学子,其前往考试的花销更大。谢肇淛在《麈余》中提到,在嘉靖时期云南每名举子的会试路费至少就要100两。
住宿费用。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交通费是一笔必要开销,此外,举子无论在路途中还是在考试地,住宿问题也是一项不得不支付的费用。赴考途中的住宿属于投宿性质,时间较短,租金较低。而士子在试地的住宿,时间较长,费用也会相对较髙。
根据张应俞的笔记小说《杜骗新书》记载,在应考士子较多的年份,租金会较高,为20两左右,以居留两个月计,则考生每月房租约为10两。在应考士子较少的年份,租金也会随之减少,约在12-15两之间,平均每月房租约在6-8两之间;在《欢喜冤家》中,有为公子在四月中旬便赶抵南京,到八月底乡试结束,在南京共居留3个半月左右时间,租金为20两,平均每月为6两多。
伙食费用。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除了需解决交通路费和住宿费外,还要解决赴考以及考试期间的饮食问题。
伙食费用上则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自行安排了,有的会较为丰富,而有的则较为简朴。在《欢喜冤家》中,扬州府仪真县秀才许玄赴南京乡试,他考试期间的饮食是由巫云负责准备,一顿酒饭便支出300文钱,开支偏高,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士子每日的饮食费用;也有的考生是食宿在寺庙、道观等处的。像是清初小说《云仙笑》中提到的,景泰年间,山东兖州府人吕文栋赴省城乡试,食宿于考场旁的道院中,开销共计数两银子。
除了待考期间的伙食需要担心,考试期间的饮食也是需要考虑到的。明初,考生搜检入场的时间在黎明,午餐有官府供应,所以考生无需携带食物入场。随着应试人数的增加,成化二年后,考生搜检入场时间提前至凌晨1时-3时,这就产生了早餐问题,所以考生会自带一些食物充饥,俗称“考食”或“场食”。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便提到,贵州都督府汤镇台的两个儿子汤由和汤实赴南京乡试,他们让人给准备了考试时早餐,“料理场食:月饼、蜜橙糕、莲米、圆眼肉、人参、炒米、酱瓜、生姜、板鸭”,还真是颇为丰盛。由于考生携带食物,不利于现场的搜检,但后来考生只能手执少数肉果进场,就不用太担心考试期间的伙食问题了。
考后的各项开销
考试结束后,对于学子考生来说还不是结束,要等到考试结果公布,才能决定他们接下来的命运。这结果不同,开销也是不同的。
金榜题名者。中举的考生,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他们要参加一系列的礼仪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酬谢为主题,开支较高,如贽见座主、犒赏报人、宴请乡邻等费用。
考生中试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即考试的主试官投“门生刺”,酬谢座主,以“确认座主、门生关系”,这就产生了门生贽见座主的费用。根据李乐的《见闻杂记》中的记载:“各具清帕四方、书一册”。在这个时候,门生贽见座主的费用较少。此后随着时间推移,该项费用逐渐增多。
根据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说:“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嘉靖时,每岁贽见费为数十两至三百两不等。而大约到了万历年间,每年费用已经增加到了600-700两。
在一个热衷科举功名的社会里,科举考试放榜后,中试者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将金榜题名的喜讯告知亲人。负责向金榜题名者走报中试喜讯之徒称为“捷子”或“报人”。报榜者走报至家,中试之家会给予一定酬金,以示打赏和犒劳。
具体来讲,报榜者事先按中试者的名次商议好价钱,等到抵达其家乡时,按所议之价索取酬金,费用为数百缗至一千缗不等。明初,各地中试家庭的报赏费大致在10两以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中试家庭的报赏费开支,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时至崇祯年间,中试家庭的报赏开支陡增至500-600两。
考生中试后,除要贽见座主、犒赏报榜群体,还要宴请族人与乡邻,以示庆贺。根据郭子章的《王父云塘先生年谱》中的记载,郭子章在考中顺天乡试和后来考中进士的时候,他的父亲郭奇美都会敬告祖庙并宴请乡人。这宴请的费用也是一笔开支,根据中试者的家庭情况各有所不同。
名落孙山者。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中试名单一经公布,大部分落第者便陆续开始返程回乡,踏上凄清的回乡之旅,但此时他们的盘费大多已用罄,其处境是比较窘迫的。根据张文麟的《端岩公年谱》中所提到的,他弘治十四年参加南京乡试,“三场毕,乏盘费,迁延数日而归”,十七年再次参加南京乡试,场毕,“是时,又欠盘费十六”。落第士子的返程旅费应与之前的应考费用大致相等,都是产生在路费、住宿费和伙食费上的花销。
而且最关键的是,一次落榜就意味着考生在此前所有投入的花销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要再次备考,就又有一笔笔和此前重复的开支。多次落榜者的开支更是难以想象。所以从表面上看,中试者的支出要大于落第者,但实际上落第者的支出要大许多。
费用的各项来源
在以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明朝的文人学子如果想要参加科举,从备考之日的聘请老师和购买书籍文具,赶考时产生的食住行等各项花销都不是小数目。落第则意味着此前投入白费,还要付出更多的花费。中试后产生的各种费用更要大于之前的延师、图书、文具、交通、饮食、住宿等费用。而且无论是落第还是中试,明朝考生的考试花销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加。
所以考中科举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固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但也为此付出了较高的成本。考生在考试中的花销所需的钱财,有些是自行筹措,也有家庭的支持和宗族的资助,此外还有社会的赞助和官方的支持。
明代官方科举考试费用构成:主要包含考生赴考路费与试卷费资助、贡院修建与维护、考务、宴赏、科举录刊刻与进士题名碑建造等支出。
那么,明代科举考试经费来源几个方面呢?刘明鑫博士也做了清晰的列举:主要有财政拨款、征派银两、学田、分摊、社会捐助等途径。其中,官方财政拨款主要有官帑、羡余、赃罚、赎锾等名目;分摊主要见于贡院修建、维护和考务费用中;征派银两主要以征派科考、乡试以及会殿试用银为主;社会捐助的主体为官绅,形式为捐俸或捐资。官方财政拨款、征派银两、分摊是基础,处于主体地位;学田和社会捐助作补充,处于辅助地位,二者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官方科举考试费用来源体系,为科举考试的顺利举行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经费保障。
经费管理制度:明廷主要通过严格预算、解运上缴、收贮待用、造册存档、监督与稽査等制度对其进行管理,总体表现出定额税制与灵活征收相补充、府县留用与解运上缴相统一、多种置办方式有机结合、适时改革等特点。
科举考试中考生承担部分:考生在备考、应考、考后等阶段,也会产生延师、图书、文具、交通、饮食、住宿、贽见座主、返程、犒赏报人、宴请乡邻等费用,除官方资助外,主要通过家庭支持、自为筹措以及宗族、社会与会馆资助等途径来解决。具体而言,家庭主要通过变卖首饰、营办治生、赠送、借款等提供支持;自我筹措则主要有教书、著书、佣书、经商、称贷等途径;社会资助主要包含试卷与文具、灯油、路费、食宿等内容;宗族主要通过创置族田、发放祠钱、经营工商业等方式,对其子弟备考与应考提供资助;会馆资助主要是指提供免费或优惠的食宿场所。
但这些考试的物质支持对于一些考生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有的难以负担而放弃了科举,也有的因为前期投入过大而在考中做官后肆意腐败。考试费用过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和负担,更是减少了社会底层人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这里边的道理也很明白,那就是社会财富的累积,使得两极分化日渐严重。科举壅塞令士子长时间无法到达成功的彼岸,而学子若长期不事生产,所消耗的科举费用日增而无有回报。科举消费在明代中后期呈现出凶猛增长态势。像上文提到的王世贞“初岁费将三百金”,那是王世贞家境颇丰不知节省造成的,但他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比之其他困于科举之途者,可算是顺风顺水了,花费三百金固然多,那也不在话下。
如此看来,一家境寒微士人若是屡次科考均不能见售,则花费肯定不在少数。若是全不顾同年、乡里官长、座主等社会交往打点之费,就是延请塾师,日常笔墨书籍灯烛,赶考路费,每一项也都是烧钱的勾当,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而一男子若久困场屋,学资不继且不说,父母妻子也不能养,贫死、饿死的阴霾时时笼罩。
所以有民间谚语说“穷不读书”,就是因为科举功名太费钱,一般小家庭难以承受。然而民间的情况却是读书多寒士,这岂不是矛盾吗?其原因在于贫寒人家一旦跃龙门,则光耀门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吸引力对于渴望改变家族命运的寒士来讲,是无法低估的。贫寒之家若得一俊秀儿郎,便是再艰难也要供其读书,而现实的残酷性又会将这些寒微士子推向更加贫苦的境地,使得他们为养父母计又不得不“弃举子业”,另谋他路。
换句话说,士阶层的社会构成改变,在明中后期,中下层庶民阶层子弟占据了士人的主体。而这一部分人群的经济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一旦从事举子业,家庭就要丧失掉一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如果士人又久不见售,则无法事俯仰,家庭生存就会面临问题。
诚然,士人可以享受一定的经济特权,这对于富裕小康之家则可锦上添花,但对于经济薄弱的庶民之家则无法雪中送炭。基层士人自身谋生能力有限,思维僵化。社会嘲讽为百无一用,读圣贤书,固然明理明德,但传统的儒家思维方式,却总是约束士人谋取更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