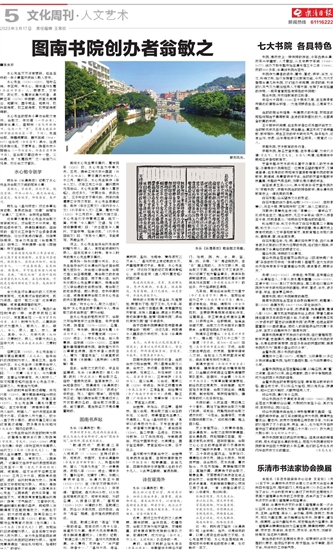书院作为儒者的读书、藏书、著述、讲学、会友、论文、吟诗之所,始终发挥着文化教育功能。今天,为大家推荐乐清几所书院,它们在办学规模、存续时间、引领时代风气及为朝廷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起来看看那些有特色的书院吧!
梅溪书院,开放性教育的实践者。
宋绍兴十四年(1144)王十朋未及第,在左原孝感井南边修建梅溪学馆,一为继续耕读生活,二是育才乡里。
当时的梅溪书馆是一所高层次的书馆,按现在的规格说相当于高等教育,生徒的年龄都比较大,也都具备较高的学问。
王十朋学识渊博,他主张学者应该先器识后艺文。当时教风学风自然炽盛、师生融洽,真正形成了亲师重教、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的学术研究风气,除本地外,还有台州、安徽、山东等地学子慕名而来,一度竟达120人。
宗晦书院,艺术教育的先行者。
宗晦书院,原名艺堂书塾,在东皋山麓。为宋代汤建(字达可,号艺堂先生,乐清人)所建,他是南宋中期知名学者和教育家。
艺堂书塾与艺术的关系基于汤建本人的艺术造诣。汤建是宋代浙南地区一位颇有名望的理学家,又精通音律,他本身的修养和爱好直接影响着书院的教育教学。乾道间,朱熹曾讲学于此。当时的艺堂书塾教学质量高,书塾的气氛活跃,刘黻也是汤建的学生。
后至咸淳五年(1269),县令郑滁孙将艺堂书院改为“宗晦书院”。宗晦书院当时的特色教学,是乐清书院教育史上一道优美的风景。
白石书塾,山溪望族文化的象征。
白石书塾的创办者钱尧卿(1073—1144),世称孝廉公,与王十朋、贾如规并称“三贤”,后人立祠纪念。
刘黻作《孝廉先生传》说:“孝廉公……建学山下,礼迎先生主之,端尘诲饬,凡三十余年矣!四方从游者至千徒,成就者甚众。”说明白石书塾当时的盛况。
钱尧卿之后,钱文子开创了白石书塾第二个高峰期。钱文子(1147—1218), 为儒学巨擘,是乐清历史上颇有成就的人文学者和教育家,其教育理念与现代接近,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
白石书塾经宋、元、明、清依旧书声不绝。古代乐清有很多这样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书院,他们世代相袭,共同创造了乐清灿烂的耕读文化。
雁山书院,独特的文化景观。
雁山书院坐落在雁荡山西内谷。《瓯海轶闻》“朱谏”条目的校笺中说:“朱谏长期卜居雁荡,在大龙湫附近天柱寺旁其子守宣建雁山书院,课徒著述,啸傲会友。”
朱谏(1462—1541),字君佐,号荡南,自号雁山主人,乐清瑶岙人。少年从游永嘉朱墨瞿(1438—1519)。正德十年(1516)其以丁母忧离任。第二年他以雁山书院作为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基地,讲学、著述、会友,很多学者、学生、官僚慕名拜访。
南屏书院,明代书院制度的典范。
南屏书院院址坐落在北白象白鹭屿村,明嘉靖八年(1529)由高友玑(1461—1546)致仕后创办。
高友玑为官四十余年,政绩卓著,持身谨慎。嘉靖八年(1529),高友玑在刑部尚书任上退休,带着几箧伴随他宦游多年的图书回乡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25岁读书时“蓄志欲创南屏书院”的夙愿。他把全部积蓄置田100亩做基金,把收入的田租供给村内青少年上学,在家乡白鹭屿开办“南屏书院”。
南屏书院虽属于家族创办的书院,但它管理规范,教学严谨。忠信慎行、博古通今是高友玑创办书院的宗旨,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四百多年后的民国时期,南屏书院改办为“南屏乡盘谷初级小学”。
金鳌书院,西乡书院的翘楚。
清嘉庆十二年(1807),郑瑞云、戈印清等20多位乡贤创建金鳌书院,始称文昌阁私塾。今为白象镇中心小学。
金鳌书院院址坐落在鳌峰山麓,以峰名院,寓“鳌”之深意。自创办以来,由名师掌教,西乡学子争相就读,成为当时西乡书院的翘楚。
金鳌书院当时有蒙馆和经馆,秉承梅溪教学的风格,重经史文学,不以科名为旨归,而以纯风俗、振儒术、知兴亡的大胸怀、大眼界培养人才。
印山书院,清代东乡名院。
印山书院创办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院址坐落在大荆镇印山山麓。大荆城内有座小山,其状如印,故称印山,院以山名。
印山书院据传由当地乡绅张桂萼建文昌阁一座、小屋数间作学舍,后又将仓颉祠合并为书院,聘请贡生曹笑山、曹志丹、拔贡方翊卿等名师执教多年,为科举时代培养了不少的生员、贡生、举人,也为地方开启民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民国二十六年(1937)改为县立大荆小学(今大荆印山中学)。
虽然书院教育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创造的辉煌成就,却永远留在乐清的史册上。那些为书院建设和书院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乡贤名儒,他们的名字也永远闪烁在历史文化的星空。(乐邑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