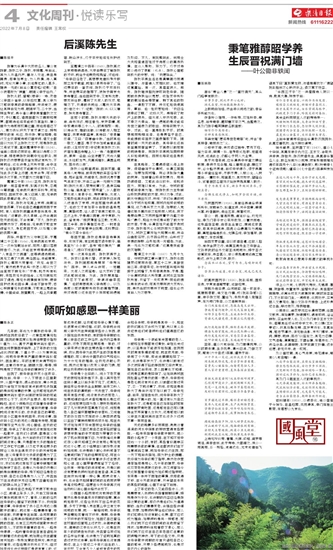陈璋为乐清十大历史名人,璋公有陈猷,陈杕二子。陈杕,字特嘉,号后溪,其为人外温内严,善与人交往,虽自身高贵,却奉如寒士,为人热情,待人真诚,无论大事小事,找他帮忙的人甚多。据侯一元的《后溪公墓志铭》记载:“自小被堪称为‘神童’,跟随父亲于任内。”
陈杕儿时,曾赋《思亲》一诗,劝告父亲回乡省亲,以祭扫坟墓。其父亲为之感到非常的奇异超群,并深爱之。便让其拜伯兄为师,跟随学习。二十岁,当庠生考试,县令潘公潢非常看重杕之文才,予以嘉奖,诸同窗都为之佩服和羡慕,都期待他将来能够及第登科。璋公晋升为侍郎而权高位重,而他却屈己下人,竭力去认识天下有才德之士,特别要好的有:钱应、杨乔龄、黄廷相等。每次文士饮酒赋诗或切磋学问,诸文士都自以为比不上陈杕之文才,可是陈杕且又连试不第。直到嘉靖甲午年(1534),省斋公因年迈而致仕,朝廷以侍郎公之功德,特恩赐陈杕到朝中充任职务,而陈杕仍然想要自我奋发而欲有所为,不肯就任。这也许是上天所安排,命中注定,让他暂时还不能敲开这贤科之门。如此多次背上行箧,赴京会考,可没想到多次不第,大家都为之惋惜不已。
嘉靖二十年(1541)正月,陈杕与兄陈猷一起客居京师,拟再次科考,忽闻令尊病重,兄弟俩只得放弃科考,疾驰而归。回到家中,其父已离人世,兄弟俩因此悲痛欲绝,伤心不已。
次年,陈杕与兄再上京师,向朝廷报告丧事,不料他自己得重病而困于京城。有人将陈杕病重消息告诉其母,其母说:“没事的,我儿孝顺,必然会得到老天的庇佑,不会有事。”不久,陈杕的病果然好了。病愈后,兄弟俩不敢在京逗留太久,急忙赶回家中,以处理父亲的丧葬大事。
丧毕,并居家为父守制三年,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兄弟俩再返京师,又一次参加朝廷会试,可两人都以落榜而告终。为此,只能在京师等候谒选。“人有旦夕之祸福”,在等候谒选期间,其兄又得了大病,虽经医治,未能康复,陈杕心痛而大哭着说:“我兄,命世之才,竟然就息于此吗?我怎么可以为了当官而不顾兄长?”于是,耗尽所有钱财,来拯救兄长的性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谒选。等兄长病情稍有好转,便亲自护送其返回乐清,沿途不辞辛劳,悉心照顾着兄长的病情,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千里迢迢,披星戴月,一路上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终于平安地将兄长护送到家。
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陈杕再次上京师等候谒选,大宗伯费寀了解陈杕的才识,就给予他鼓励和挽留,对他说:“母亲已经老了,再想要凭借科考升职而立足于朝堂,就难以孝养母亲了。”经过费寀的一番劝说,陈杕终于放弃科考,并在费寀的推荐下,被授予南京光禄寺署正。当他回到家中,又有所犹豫,想放弃任职,遭到了太淑人的反对,勉强之下,只得前去就任。《嘉庆太平县志》卷之十(下)记载:“陈袱(杕)以父璋恩,授光禄寺署正。”
在那个时期,陈杕与卿大夫的子弟、尚书刘讱、卿汪春元、京尹李镛、郎中黎遵训等二十八人,时常相聚一起,以诗会友,雅韵流觞,以诗歌与人相互赠答,共享诗歌盛宴。其诗曰:“忠孝肇兹酒。”又曰:“图意垂千龄。”当时其他一般文人墨客,是不予参加或偷看此盛会的。《玉环厅志》中记载有陈杕之《秋夜宿龙潭古寺赠上人》一诗:“绝壁俯寒湫,禅房一径幽。山空凉露下,天近火星流。水壮蛟龙气,风高鸿雁秋。清圆坐明月,若与远公游”。
陈杕公任期届满后,回到家里,值其母八旬寿诞,前来祝寿的宾客络绎不绝,斑彩盈庭,热闹非凡。陈府沉浸于喜气洋洋之中,方伯二谷侯一元特为之撰写《陈氏太淑人荣寿叙事》文,邑侯石峰杨公錀,扁其堂为“荣养堂”,乡人都称赞太淑人有孝子也。寿辰事毕,太淑人又勉励他再去任职,而此时陈杕已派佣人送信去了京师,并在那里守候消息了。他的文才有如李令伯般的温柔宽厚,真挚诚恳,让人读了非常之感动,经三次上书,于是得以同意,并予复职。为此,留有诗:“秣陵薄官经三载,乞养人回又半年。游子情惟慈母恋,一封恩自九重怜。”时有缙绅士阮鹗、沈科赞曰:“君今之李令伯也!”
每回家里,陈杕总是亲自侍奉其母,片刻不离。有空就居家读书教子,扁其室为“小小轩”,自号“翔云樵夫”“ 镇海渔父”,闭口不说官场事。
有一次其母生病,陈杕哀祷于上天,祈求以自身代替,夜梦神人授笔与书,陈杕随即起身题写“母寿延长”四字,神人点头许可,一觉醒来,太淑人之疾痊愈,让大家听了都对此感到诧异。为此,陈杕题其楹:“母慈不下俞郎杖,帝德深垂李密情。”他时常想起其父亲侍郎公,以及侍郎公那被朝野所称扬的高雅节操,并对侍郎公还未祀于乡贤而感到遗憾及愁闷。不久,有阮鹗到此,利用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对于侍郎公的高涨热情,在众人帮助、努力下,终于对侍郎公进行了表彰(祀典),陈杕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说:“我愿毕矣。”
陈杕平常生活总是清廉简约而遵从操守,与普通人家相比较,他家境还算富裕。有一次,其居室被火,起先,陈杕唯独担忧惊吓到老母亲,随即前去搀扶给以宽慰,收拾家中所珍藏的朝廷诰命等荣誉,剩下其他的物品,一律抛下不顾,并匆忙地快速离开。事后,他一脸欣慰地说:“我已经很幸运了啊。”这场火灾,虽导致了财产上的损失,但太淑人安然无恙,此不幸之大幸矣。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将先世之画像及时取出,而导致毁于火中,对此,他一直是耿耿于怀,时常想起而呜咽流泪,总是责怪于自己,未能提前将祖宗之画像摘取下来。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消逝,其母亲也逐渐年益高而智益衰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明辨是非,则陈杕平常就如同哄婴儿似地伺候她,因而也导致他自身极度疲惫。
在其晚年,又遭遇倭寇从海上劫掠,倭寇垂涎于乐清城。乐清三面阻山,如要加筑城墙,则必须拆除大量的民房;如顺着山势深挖壕沟,用来防御倭寇,又感此沿线较长,将耗资巨大,而难以承受。为此,守城的官员感到非常为难。而陈杕极力主张顺山势挖阱御敌的方案,并以力争。对此,前太守提出反对,并说:“我们乐清的城池处于城外地势高,而城内地势低矮的情况,这乃是兵家之大忌,如果敌人凭借这样外高内低之地势而入城池,岂不是要白费二万两民脂民膏于沟壑之中吗?”最终,现任太守还是采取了前太守的方案。于是,乐清百姓只能居于危城之中,陈杕每天心系城防而为之担忧。不久,城防工事开始大规模兴起,并沿山凿取石材,伐尽四山树木,山岭成了赤裸的原野,山形地貌一片赭色。为此,侯一元也为之感叹道:“这真是贤能者的灾难啊。”
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十九日,守城防御工事兴建不久,陈杕也因操劳过度而去世,享五十二岁。其辞世后二年,倭寇来犯,与守城官兵短兵相接于土城墙下,形势非常危急。于是,整个乐清城被战火所笼罩,此城也正如陈杕所言,只留下一片叹息声!而他的提议虽未被采纳,可其效果则被大家所认同,虽然当时效果并不明显,但也必然有后人为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