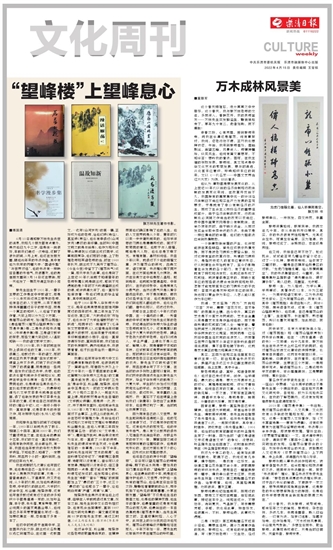4月10日得知滕万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和几个朋友都有点意外。虽然他已九十二岁,但身体一向很好。年前我们通过一次电话,还聊了很长时间。3月上旬,他还在发朋友圈,晒他近年来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他为我写的两幅大字:“国语书塾”“与世界对话”。他的书法有一种跌宕自喜的书卷气,我很喜欢。他的微信朋友圈到3月14日还在更新,那一天他发了一棵花开得正好的小视频。
滕先生出生于1931年,一辈子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学教语文,却是一个从未放弃过独立思考的老师,他有自己的人文世界,从来不是那种浑浑噩噩过日子的教书匠,而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人,从他留下的著作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雁荡山的研究,如《雁荡山揽胜》《漫话雁荡》《雁荡山楹联赏析》《雁荡漫步集》等;二是书法和书法理论,《书学漫步集》等,三是语文教学的探索,那些文章大致已收入《温故知新——我的语文教学文存》。
大约1979年,我少年时就在刊物上读到过他的文章,1982年,我读高二,他教过我一年的语文,那时候他正热衷于提倡“启发式教学”,课堂上并不多讲,打破了我们长期习惯了的满堂灌,而是提出一些问题,启发我们自己去学、去思,他的做法也曾引起许多怀疑和议论,即使在学生中也颇有一些不满,我是赞同他的,也是课后经常去他办公室找他求教的同学之一。我最早知道元代文学家李孝光就是在他那里,读了他新发表的考订李孝光生卒年的文章,还有他自己刻钢板油印的《雁山十记》,这一油印小册子我一直保存着,这是李孝光的传世之作,可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媲美。
我和滕先生相处时间不过短短一年,1983年以后就失去了联系。相隔二十四年,直到2007年,我们才重续师生之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我们的交往一直没有断过,他每有新作问世,总会寄给我。有一年,我回他当年教我的母校大荆中学讲座,不知他怎么知道了,一定要来听,而且两个小时一直听到底,当时他已年近九旬。
我在闲聊时几次建议他写回忆录,他总是说自己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值得写。我又劝他说,从少年时代起,比如他所遇到的老师,中学时代的胡兰成,大学时代的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等,还有他写信求教过或有过交往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值得一写的,比如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承焘等,更不必说同乡的画家周昌谷等人。他说自己多年来零零星星也写过一些,如果收集在一起,恐怕差不多有一本了。
他初中时就读于淮南中学,正在国共内战之际,胡兰成化名张嘉仪逃亡到雁荡山,在这里一边教国文,一边写《山河岁月》的第一稿,正好成为他的老师,给他们讲《诗经》,甚至讲《易经》。他也有幸读过《山河岁月》最初的油印稿,当时叫《中国文明之前身与后身》。他作为班长还带头罢课抗议过胡兰成打同学,这事起因复杂,他们那时幼稚,上了物理老师和英语老师的当。时在1948年秋天,胡兰成不久离开了雁荡山,《今生今世》中留下了《雁荡兵气》这一篇,却只字未及此事。他也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知道昔年的老师张嘉仪就是胡兰成,感到不无遗憾的是少年时不大听得懂胡兰成的课,或许讲得太深了。他一直好好地保存着一张他们师生的毕业留影,其中就有胡兰成。
他于1956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晚年他常常想起在丽娃河畔度过的四年时光,第二年发生了反右运动,第三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了,他也参与了大学生编教材的“大跃进”,和同学们一起编写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这曾是当年印刷量很大的教材,他后来羞于说起这本印制粗糙的小册子,但他一直保存得好好的,直到四年前,我们在他家的书房聊天,偶然说起此书,我很想看看,他才找出来给我一睹庐山真面目。
我建议他写写华东师大中文系对他最有影响的老师,他很快就写了一篇寄给我,可惜因为涉及上个五六十年代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这篇题为《华东师大三先生》的文章一直未能发表。他心目中的“三先生”是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他说徐中玉是他大一时的文学概论老师,六个班级二百多人一起在大礼堂上课,用的教材是徐先生自编的《文学概论讲稿》,却是讲一次,改一次,并不是照本宣科。他说起徐先生从1957年7月下旬以后开始挨批,面对不合事实、上纲上线的批判,仍会在恐吓中据理力争。先后给他们开过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专题课的钱谷融先生,在他入学第二年因发表那篇名动一时的《论“文学是人学”》,遭到猛烈批判,虽侥幸没有成为右派,却一直做了38年的讲师。钱先生的课深受学生欢迎,令他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59年下半年,他听钱先生说到“艺术的起源”,他在听课笔记中记下:“诗歌舞三者同源: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旋律,舞蹈可以没有姿态,但三者相同的一点是,都不能没有节奏。”听课笔记发还时,他发现细心的钱先生在“诗歌”“音乐”“舞蹈”的前面都加上了“最初的”三个字,这三个“最初的”让他感念了一辈子,让他明白何谓“严谨”、何谓“认真”。
施蛰存先生虽然没有给他上过课,但早在入学前就读过其文章,反右之后,施先生到中文系图书馆打杂,他有机会当面请教。直到1997年他为研究朱熹的一篇文章还写信向93岁的施先生求教,通过三封信。(以上内容来自:滕万林《华东师大三先生》未刊稿)
他对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这些老师的敬重是由衷的,在精神层面他们确实影响了他的人生。他的人文世界就是从少年、青年时代以来一步步建构起来的,他好学深思的习惯也是慢慢养成的。面对不敢苟同的意见,他敢于与人商榷,哪怕是大人物,他也总是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拿材料说话。我自少年以来,就读过不少他的商榷文章,涉及雁荡山的研究、古典文学、语文教育、书法理论等不同方面。在这方面他颇有几分愣劲,虽然在日常交往中他是那么温和。越到晚年,他就越发显得温和。中年时代,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颇有几分傲气的。当然这傲气只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并不是刻意的,跟我们这些学生交往,他还是随和的,我们到他那儿翻他的书,他也让我们翻,借书也可以,还送过我书。
我感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一所普通的中学还有滕万林先生这样的老师,我记得当时华东师大毕业的语文老师就有好几个,还有鼎革以前毕业于大夏大学的历史老师,肄业于老浙大的数学老师。他们以诚待人,学业严谨,上课也不是从应试、解题入手,而是着眼于求知的本质。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概念,那时候似乎还没有浮出来。老师就像老老实实在知识园地里耕耘的农夫,滕先生不仅研究语文教学,而且在课余写了不少文章,在当时的许多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教我们历史的蒋祥贞先生比滕先生大两岁,毕业于华东师大的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学生时代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运,参加过民盟、土改运动,做过校长,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我一直忘不了他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新青年》杂志出了全套影印本,他自费订购了一套,当时就让我羡慕不已。
因为拥有自己的人文世界,滕先生越到晚年活得越从容,他的笔从没有停下过,不仅是写作的那支笔,还有他书法的那支笔,他的字有书卷气,是从有文化教养的读书人笔端自然流淌出来的,与职业书家的字不大一样,横撇竖捺之间没有那种刻意的经营和做作。他是研究书论的,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心得,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想法。
他将自己住的房子叫做“望峰楼”,日日可以望见雁荡山的嶙峋奇峰,脚下的溪水则是一碧如洗的石门潭流出来的。“望峰楼”上望峰息心,他在最后的数十年,就是在这里守护他的人文世界,守护他一生所爱的雁荡山。他经常在日出日落之际,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山水,用手机拍下他所见的朝朝暮暮,分享在朋友圈。“望峰楼”不仅是他生活的栖居之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生平的著作,他最看重的还是有关雁荡山的那几种,他最后出的一本自选集就是《雁荡漫步集》。当先生离世之时,正值疫情封控、人心不安,此刻世上的纷纷扰扰已与他无关。雁荡山的群峰依然静静地站在那儿,千年万年如一日,愿先生就这样悄然安息在雁荡山的呼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