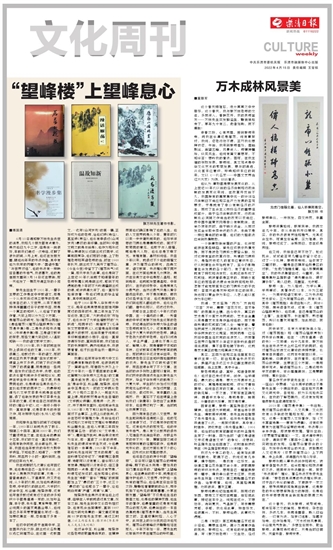这个春天特难忘,缘分冥冥之中安排好。这个春天,我与滕万林老师的交往,多而深入。春暖花开,我的良师益友——万林先生突发脑溢血,静悄悄地走了,享年九十有二。逝者如斯,岂不痛哉!
仲春之际,心有灵犀,接到滕师来电,问我在乐清还是雁荡,说有事探讨。我说,您老行动不便,正巧我也想拜访您。午后,我来到滕师居处,屋临荆溪,斋望五峰,风景迷人。师精神瞿烁,谈笑风生。他说有篇文章想写,不知妥否?想听我的看法;若可,在我主编的刊物发表。滕师说,其文观点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要与时俱进,淡化官本位意识,呼唤知识本位的到来。文以《一代名家——中国文艺界当红六大家》为例,谈谈看法。
他认为:事物都是要发展变化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发展变化来说。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适应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于是就有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体制的改变,行政体制也必须随之作适当的改变以求适应。像中国书画黄页网等非公有制载体,在举办贺年历时,由于缺乏资金,从而对发奖金采取半卖半送的办法,未尚不是一种应情适时的举措。他们的大胆做法应受到热情鼓励。
一个新事物新举措的产生,也许可能存在某些缺陷。首先应该表示热情支持,而不是被老习惯势力蒙昏头脑,反对这种有益的改革行动。所谓的习惯势力,是指历史悠久的官本位意识形态。它从封建社会开始就有了,至今仍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部门。有了官本位,就有了特权和决定权,也就逐渐形成了权威性。就被看做是正宗的,而缺乏官本位的那些做法便会受到歧视和贬抑。怎样才能克服官本位的习惯势力的干扰呢?答案只能是欢呼知识本位的到来。货币可以黄金作为本位,人怎么能以官作为本位呢?
我道:艺术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与土壤。古今中外,真实的艺术是不分官方与民间的,艺术含金量从来是靠艺术本身作品说话的,而不是由所谓的权威部门或人士一锤定音。譬如民间艺人阿炳的《二泉映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阿炳是一位经历旧中国生活坎坷的流浪艺人,然而著名世界级指挥家小泽征尔在聆听此曲时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跪下聆听。这就是艺术真正的魅力和真谛之所在。
其实,正因为在现实生活里官本位意识主宰一切,故出现某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产生多达三十多位副主席的笑话闹剧。当上主席,其字千金。
滕老师闻此语,直呼,知吾者联军也!他对自己走过求学,创作,治学道路,最大的心得是:要大力开展学术上的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谬论才害怕揭穿。他说自己写的文章,也只是个人的新见解,一家之言,不敢妄言正确无误。提倡学术争论,是明是非,辩美丑,分善恶的大好事,而不是坏事。
回首往事,滕师一直坚持自己学术精神。他在读大学期间,写信给丰子恺先生,请教美学问题,丰先生向他推荐了朱光潜先生。后来,他与朱光潜先生共通信了6次,一起探讨美学。其中有2封信件,被收录在《朱光潜全集》。1964年,他给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语文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的争论,没想到,叶圣陶先生给他回信了。这封信后被收录在《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中。
我对九十有二的老人,能有如此襟怀和眼光,敬佩不己。我说还有几件事,请予相助。一是我有一位好友,金华浦江著名花鸟画家徐小丰,很敬佩滕师的学识与书法,想用自己一幅画换滕师一幅字,请我牵线做艺术红娘。我把徐先生刊登《东瓯》第三期翰墨名家的作品,给滕师看,他说,其画格调高雅,功底很深,喜欢互藏。
滕师说最近记性差起来,刚用过的东西,想用又不知放在哪里。怕忘把此事,特记在本子上。说现在还冷,不想动手,待到夏天,气温暖了,写字需要灵感,手感。我也将此事,转告好友,他很高兴。不料,滕师仙逝,此事成为遗憾。
二是《东瓯》第五期翰墨名家栏目介绍他,需要生活照,简介及得意作品的挑选,滕师应允。还有他的学生傅国涌,写《滕万林老师》一文生动,经过滕师牵线,一并刊发,图文并茂,丰富全面。
滕师深情地说,联军贤弟,我俩交往几十年,你从未向我开口题字。其实,你的书法很有灵性和雅气,尤其还会左书,可谓左右逢源,实为难得。我说,滕师过奖了,涂鸦而已,志在修身养性。
他又说,我怕自己写不动了,趁这机会,试试能否写几幅给你留个纪念。过了一个礼拜,滕师来电说,给你写了二幅对联,一幅是自己撰写仙桥景区的对联,“龙虎门雄踞北麓,仙人桥横跨高空”。我的书法集曾出过,今重写;另一幅是集叶圣陶联语“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斯人已逝,见墨宝,尤伤感。
滕师一生,为人坦诚,为学认真,学养兼修。其著作达12本,分为三部分。一为美学和语文教学;二为书法和艺术评论;三为写雁荡山的,共有5本。其中《雁荡揽胜》连续出版6次,共计6万册,颇受读者欢迎,还有一本《雁荡山楹联赏析》。他笑道,自己是雁荡山的“土著”,生在雁荡,长在雁荡,熟悉雁荡,所以也喜欢写雁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对《雁荡揽胜》和《雁荡山楹联赏析》两书评价颇高。他在“《两本值得一读的书》一文写道:近十几年来,滕万林先生在书法艺术上成名成家的同时,他对雁荡山旅游文化建设的独特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两本书面世以来,一直畅销,口碑很好。在我看来,他对雁荡山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用美学观点,解读雁荡山水;二是运用书学家的眼光,评价摩崖碑刻;三是慧眼识珠,填补空白。”
著名作家许宗斌先生在《一个人与一座山》中赞道:“山水美学的概念不是滕先生第一个提出来的,但在地方风景文化研究中,自觉地、较为系统地去实践,在我的了解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有谁像滕先生做得那样好。”
2019年《雁荡漫步集》一书出版,是对雁荡山的美学、人文风情、文化历史有众多新的挖掘和发现,进一步补充,这是一本雁荡人文好著作。如《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没有收录康有为在雁荡山留题的诗词、书法等20余件作品,却被滕师挖掘,替补空白;《怀素雁荡留墨宝》一文,在点滴中寻找线索、得到怀素《草四十二章经》这一突破性的发现,经雁荡山管委会的介绍,引发中央电视台的关注,被拍摄成人文纪录片《怀素与雁荡山》上下两集,走上央屏,深得国内外观众好评。
滕师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被誉学者型书法家。他采取理论和技法兼修之法,把美学与书法融在一起,探索“书法美学”理论。著名书法家张索先生评道:“滕老因其深厚的书法理论积淀,对于古代书论的解读,不局限于一家之言,思考问题的视角常出新意,这是滕老的书论思想保持活力的原因,也是他的书学思想拥有全新视角的根源之所在。”
这个春天,我与滕师,或聚或电,感受忘年之交的愉悦。滕师说,杂志出刊,多送几本。未闻油墨香,斯人已仙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万木成林风景美,千山竞秀气象新。”多想左右而书,敬给滕师。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天堂书香,滕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