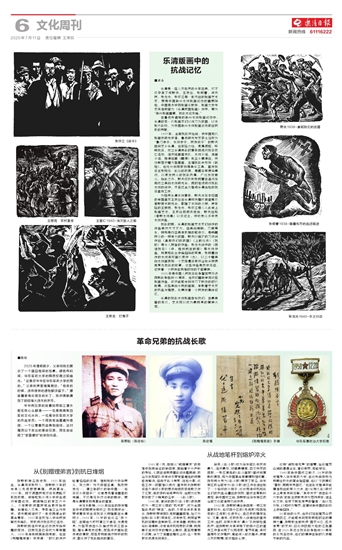陈野耘(陈定标)

陈定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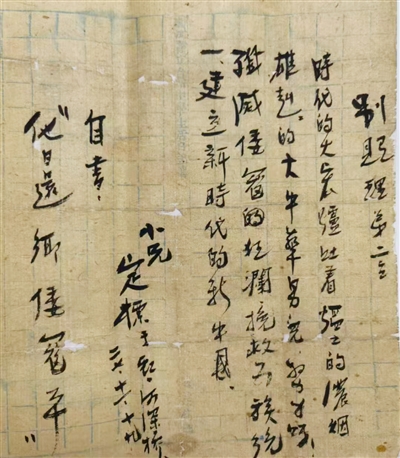
《别赠理弟言》手稿

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校徽
革命兄弟的抗战长歌■陈权
2025年清明前夕,父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包裹。褪色布料间,华东军政大学的铜质校徽泛起幽光。“这是你爷爷在华东军政大学时用的。”父亲的声音难掩激动,“他走的时候,连件像样的遗物都没留下。”摩挲着被角处斑驳的补丁,我仿佛触摸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爷爷两兄弟的故事如同瓯江潮水般在我心头翻涌——一位是皖南新四军的文化尖兵,一位是华东军政大学的热血学员;一个用铁笔油墨痛歼倭寇,一个以青春热血铸就信仰。这对雁荡山下走出的革命兄弟,用生命诠释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
从《别赠理弟言》到抗日烽烟
陈野耘原名陈定标,1921年出生,乐清河深桥村人。陈野耘少年时受其父先进思想熏陶,倾向革命。1931年,因不满国民党对日本侵略不抵抗政策,领导虹桥沙河小学学生进行爱国运动,跟随响应的有五六十人。少年野耘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学籍,后借他人文凭,考取省立台州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1937年在校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陈野耘因组织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的那刻,已预见自己将成为燎原星火。1938年奔赴皖南新四军前,他在《别赠理弟言》中写道:“时代的洪炉吐着焰焰的浓烟。雄赳赳的大中华男儿,努力呀!歼灭倭寇狂澜,挽救民族统一,建立新时代的新中国……他日还乡倭寇平!”这首浸透着油墨香的诗篇,不仅是兄长对幼弟的期许,更是乐清青年投身革命的宣言。
受兄长影响,1925年出生的陈定理在中学时期便发起成立"励志同学会",带领青年学生将抗日火种播撒在乐清城乡。1944年,19岁的他化名“陈少旺”,在南岳大崧村建立交通站,发展党员,为括苍游击纵队输送物资三百余担。据乐清党史记载,那些深夜里秘密传递的情报,那些黎明前悄然转移的物资,都化作了抗战胜利的基石。
从战地笔杆到熔炉淬火
1941年7月,刚刚从“皖南事变”的劫难中挺起脊梁的新四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七团在结束蒋营战役休整期间,政治处发现部队中有许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亟待解决,但由于战斗频繁,驻地分散,这些工作一时都难以进行。宣传股长陈野耘将自办油印小报的想法向团政委吴载文作了汇报。吴政委听后连声叫好,当即为这张报纸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战斗报》。
1940年,首创的团级《战斗报》很快便成为一师三旅七团的“机关报”,成为全团指战员的“喉舌”。当时,办报条件极其恶劣,陈野耘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为出版《战斗报》而奔忙,没有铁笔,就用留声机的旧唱针自制铁笔;没有油墨,就用松枝烧松油调制;没有油印机和橡胶滚筒,就用刷子在刻好字的蜡纸上刷印,甚至用臂膀代滚筒,涂匀了油墨在蜡纸上印,让一张张报纸迅速发到连队。
后来,《战斗报》成为华东部队中历史最久、组织最好、印刷最精美、图文并茂的团报。一张五套色的《战斗画报》曾送到莫斯科展览,现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陈毅司令员为《战斗报》题写了报名,华东军区政治部专为《战斗报》的工作总结出版了一个铅印的小册子。这份用油印机和战士们的热血浇灌出的刊物,曾送往莫斯科展览。新中国成立后,陈野耘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准师级创作员。
1942年,陈野耘调任新四军一师三旅宣教科长,他对四分区的《先进报》和四地委的《江海报》也很关心,自己积极撰写社论、文章、通讯,还积极投入创造性的宣传工作。当时,日军伪军与“清乡”队封锁检查极严,但陈野耘与其领导下的四分区的宣传工作者采用了戏院海报、春节年画、连环画等形式作掩护,竟能深入敌伪据点,使群众欢欣鼓舞,敌伪胆战心惊。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智慧,恰似雁荡山涧的潺潺溪流,看似柔弱,却能穿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24岁的陈定理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在这所由陈毅元帅兼任校长的革命摇篮里,他以"文武兼修"著称。同期学员回忆:“他在战术推演中能精准标出敌军火力点,在《论持久战》研讨会上常有独到见解。”其中关于“游击战十六字诀”的批注被教员作为范例讲评。结业论文中,他写下掷地有声的誓言:“当以笔为枪,以知识为弹药,在建设新中国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雁荡山顶俯瞰瓯江,仍能感受到那股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陈野耘生前所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训,已化作瓯越大地的红色基因。在202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他们的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