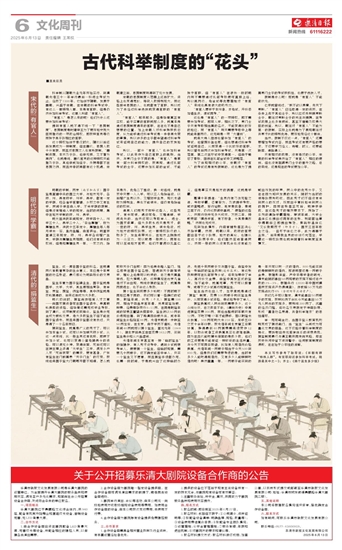■直良巨员
宋代的“有官人”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它始创于隋朝,发展于唐朝,兴盛于宋朝。在宋朝的科举考试中,有这么一群特殊人群,本身有官职,但是仍然参加科举考试,这群人叫做“有官人”。
“有官人”是怎么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
提到有官人就不得不说一下“恩荫制度”,恩荫制度是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安抚大臣而推行的一项政治特权,即按照官员等级而授予其子孙相应的官职。
这个特权始创于秦汉时代,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但在唐代,恩荫人数十分有限,而且对恩荫之人也有所限制,“唐制资荫,本只及子孙,他亲无预,又不著为常例”。也就是说,唐代官员的这种特权只能推及子孙,其他亲戚如侄子、外甥等都不在恩荫之例,而且并非时常都有这个机遇。宋朝建立后,恩荫制度则得到了充分发展。
宋朝的恩荫制度从范围上逐渐扩大,资格上也变得宽松,导致人数特别庞大。而这些接受恩荫的人,也就都有了官职,所以成为了未经过科举选拔就获得官职的“有官人”。
“有官人”越来越多,但是毕竟真正有实权、能干实事的官职就那么多,就算本身通过恩荫制度得来的官职,往往也不是自己想要的位置。加上宋朝人对科举持积极态度,认为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以许多的士子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家族地位。
所以,一部分“有官人”也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作为自己官职上的跳板。当然,与寒门士子不同的是,“有官人”是享有一部分科举特权的,按常规,通过礼部考试的士子,还要参加礼部的诠试,才能授予官职,但“有官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则不需要通过礼部考核便可直接上任,所以跳两级、免诠试等优惠措施对“有官人”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有官人愿学于本州者,亦免试,升补悉如诸生法,混试同考。”
这也是“有官人”的一项特权,即不需要参加考试,即可入学。相比之下,寒门士子只有考取相当高的名次,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地位,而“有官人”则只需要考取中上等就能连晋两级,这无疑是一项“大福利”。
就连大诗人陆游也曾参加“有官人”的考试,他曾荫补登仕郎,但也想通过科举考试证明自己,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官职,所以曾先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只是第一次落第,第二次在厅试中获得第一。但由于触怒了秦桧,陆游在礼部诠试中又被黜落。
为了体现相对的公平,宋朝对“有官人”的考试还是有所限制的,这也是为了提高寒门士子的考试积极性,也便于选拔人才。
限制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官人”不能做状元。
仁宗就曾说过,“朕不欲以贵胄,先天下寒畯。”“有官人”已经取得一定的资历,在条件上优于其他士子,所以应该先照顾寒畯士子。朝廷对寒畯士子的关注与提携,在考试政策上也多有倾斜,甚至不惜触及权贵大臣的利益。所以,朝廷对“有官人”不能为第一的限制,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展现朝廷对贫寒才俊的特别优待,更好地笼络这个群体。
当然,限制不仅这一点,“有官人”还需要增加考试内容,而且考试还有更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学习经义、诗赋、时义,还要能断案、通晓律义。
只有相对的政策,没有绝对的公平,宋朝的科举考试虽然给了“有官人”相应的便利,但也没有阻碍寒门士子的晋升之路,总的来说,还是现在的考试更加公平。
明代的“学霸”
明朝的学制,两京(南京和北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与地方无干。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都有一定的学额,归各省学官管辖。乡村之中又有社学,民间子弟自由入学,不受学额的限制,但是没有强迫入学的规定。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州、县学。
明太祖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洪武十五年定令,廪膳生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由官供给。明宣宗宣德三年规定,府、州、县学各设增广生员,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他们没有领米的权利,但是和廪膳生员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一句话说,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除徭役。以后增广生员以外,又增附学生员,现代术语称为特别生,虽也不能领米,但仍有免除徭役的权利。
通常人们用秀才称呼这些人,这些秀才,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长的,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为国家做事;但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县学生员,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层。这一群特权阶级的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众实力,可以欺辱一般民众,同样也可以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孟仁义,但是事实只是地方的祸害,这就是学霸。
嘉靖十年提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妄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查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便指的这些人,然而行动并无多大成效。万历二年,特敕吏部“慎选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然而也无成效。
见到如此情形,内阁首辅张居正决心尽除学霸。然而,明朝以来,政府的官吏都出自于这个阶层,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手中。他们固然压迫普通民众,然而一般的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因此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的反对,反而出乎意料地受到民众的拥护。因而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亲政,在这些秀才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一系列的清除学霸措施。崇祯年间,大学士温体仁也提出过同样的主张,刑部都给事中傅朝佑立即提出弹劾,奏疏称温体仁“又议裁剪茂才(即秀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为得罪于圣贤。”后来剪裁生员的计划终究落空,学霸这一特权阶层也就伴随着科举制度至其覆灭。
清代的“捐监生”
监生,这一源自国子监的科名,在明清两代承载着复杂的社会意义。本应是十年寒窗的功名象征,最终却沦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品。
监生本意为国子监肄业生,国子监就是国学、太学、大学。其生源相当复杂,有举监、贡监、荫监、例监等等。其中例监就是花钱捐得的,后来逐渐成为大多数。
明代初创时,捐监尚存培育人才之意——向国家捐资者可在国子监读书,虽属银钱换取的资格,但毕竟还需完成学业考核。到了清代,这项制度彻底异化,监生身份完全成为银钱交易。绝大多数监生不但不能在国子监读书,而且连国子监都没有去过,只是得了一个名目而已。
捐到监生,就算是广义的秀才了。可以参加本省乡试,还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从这一点来说,比一般生员还有优势。即使不参加乡试,也可以获得公堂免跪县令的资格,可以混充乡绅,获得体面。死后还可以在神主牌上添得“太学生”三字,满足小户人家“死后哀荣”的需求。更有甚者,广东有监生在门前高悬“天子门生”的灯笼。按说他连国子监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怎么就敢称天子门生呢?因为他虽未踏入监门,姓名却录在国子监名册。若遇到天子辟雍讲学,理论上他是可以听讲的。总之是天高皇帝远,拉大旗唬人的。这种情况在近京几省绝对不会出现,别说你捐的监生了,就算是两榜进士,也不会这么张扬。
捐个监生到底要多少钱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确切的记录。乾隆年间,俊秀(平民)捐监需108两,相当于四品京官年俸,另缴部监饭银、照费、经费等杂项约8-11两。在同是乾隆年间的甘肃王亶望贪腐案中,监生被以50两低价违规出售。到了晚清因白银外流,咸丰年间监生价格降至88两。光绪末期进一步跌至50两左右。在北京,由于学历不值钱,光绪年间40两就可以捐个监生。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罗田县王吉臣花费163.2两,买到监生身份和从六品虚衔。
光绪年间北京甚至有一种“临时监生”的骚操作。有人秀才没考中,遇到乡试就想考举人,便要捐一个监生。但临时现捐,需要几十两银子,还不确定能否中举人,只买一个监生又不愿意。而且捐监手续都办完,也需一段时间,于是就兴出了这种临时办法。先把十来两银子交与国子监,由监中发给一张临时的监生执照(通称监照),有这张执照便可在礼部报考乡试。将来如果中了举人,再行补交全费,由监中再发正式的监照;如不能中,就算完事,秀才可以接着考,或等下次乡试再行现捐监生。
监生当然也出人才。左宗棠就是通过“捐监”制度,花费108两银子购买监生身份,从而获得乡试资格,幸运地考中了举人。
捐监换算成人民币到底需要多少,这个众说纷纭,总之数目不低。《儒林外史》中周进捐监花费200两,而他当塾师时年薪只有12两,不吃不喝17年才能攒够。若以乾隆米价折算,108两可购大米216石,足够五口之家十余年口粮;按光绪年间北京雇工日薪计算,挣得最低40两捐费需连续劳作12年。以物价或者工资换算其实也很难准确,因为在古代能吃精米细面的是极少数,他们的工资更是只能保证一种较低的生活质量,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有人用猪肉价格换算,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500到800元。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当时有多少人能吃得起猪肉,又有多少人能顿顿吃猪肉呢?虽然重量一样,一两银子能买到的是一年只可以吃一次的猪肉,800元能买到的是顿顿吃的猪肉,那很明显还是一两银子金贵。根据彭泽益、严中平等学者的研究,清末能随时拿出50两现银的家庭不超过总户数的2%-3%。根据央行《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存款超50万元的家庭占比约4%(含理财等流动资产)。
我们几乎可以推定,清末能拿出50两银子的家庭,按照比例不会比今天能拿出5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多,更别说200两了。沉重的经济门槛,将功名交易限定于绅商阶层,形成“富者功名易得,贫者科举难求”的恶性循环。
举一斑可窥全豹,当国子监从教育机构蜕变成了捐纳衙门,当“监生”头衔成为可量化交易的商品,这不仅昭示着科举制度的异化,更折射出传统官僚体系的深层危机。捐监制度最终与清王朝共同走向末路,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警示:任何教育制度的溃败,往往始于公平性的消解。
本文写作参考了耿哥说:《宋朝有群“特殊人群”,有官职却还参加科举考试,陆游是其中之一》;齐士:《捐个监生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