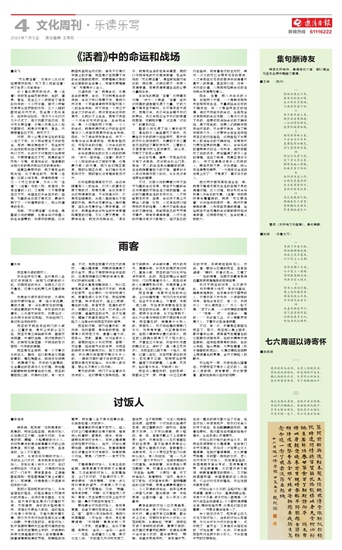早年间,虹桥街“石板是滑的”。赶集时,别说各路客商,就连讨饭人也如同过江之鲫。沿街乞讨的,多半是软犊、瞙瞠、少胳膊腿的外乡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沿街匍匐乞讨的丝虫病患者,那双腿,粗得像大象,血淋淋的,让人不忍直视。
当然,也有好手好脚的讨饭人,平时会上门乞讨,其中就有本地的讨饭人。本地也有人到外乡乞讨,他们会谎称出去“讨生活”,仿佛把讨饭当成了一门手艺;更有甚者说,江湖谁都能闯吗?那些都是睡瓦背上受露水的人!那神情,仿佛是刚从天涯倚剑归来的大侠。
那时沦落到虹桥的讨饭人,多半留宿在修船社。修船社建在七村洞河口的河滩头,沿河还有木器社、水龙社,但只有修船社是没门没墙的瓦房。瓦可避雨,待修的木船就是大床,河滩也方便生火做饭。但修船社终究是个中转站,不宜长期安营扎寨,因为天天来讨饭的老面孔总会遭人白眼。于是过些时日,有些讨饭人趁夜色辗转蒲岐片区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后来我在蒲岐上学时,夜间常听到侯宅祠堂里的讨饭人在练唱道情,随着道情筒枯燥的节拍,那嘶哑的说唱声,倾诉着人生不幸与世事沧桑,也渐渐地潜入我的梦乡。
唱道情的按说属于卖艺人,但人们对上门唱道情的总是不耐烦。谁有闲心听着呢?都是抓一把米,或倒一碗剩饭赶快打发走人,本质上唱道情已被归同于讨饭人。当然,讨饭也得带饭碗,道情筒是行头,抱着道情筒总比仰着空手乞讨有面子,毕竟那是个行当,更是一门技艺——有艺不愁穷呐。
不唱道情的讨饭人,也有各自的能耐。典某是属于那种既不会唱道情,又没能耐的讨饭人。他笨嘴拙舌,上门乞讨时,不晓得讨好人家,伸手便说:“问你搝哪。”没有一点儿可怜卑微的语气,仿佛是人家欠他的。见人家不搭理他,又说:“覅啬,有来有去哪。”天啊!这不是在咒人家吗?莫非人家往后要反过来上他家讨饭?碰一鼻子灰就在所难免了。
要说最会讨好的讨饭人,非贤某莫属。他舍不得叫老婆全名,只叫单名“香”。香可从来没挨饿过,是因为贤某嘴甜,人家给他一把米,连忙弯腰道谢:“珍珠啊!真是发财人家……”人家抓一把番薯丝,他也不嫌憎,连声说:“金条——金条——金条——”况且,他很懂女人心理,常对女主人说:“我的香几天没吃东西了,香体弱,经不起饿啊。”女主人知道他在说谎,但想想一个讨饭的也晓得疼老婆,就红着眼去打一碗热饭。香脑筋不好使,从不开口道谢,像个哑巴。有一年,香竟然戴上了上海牌手表!当然,只是她老公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空表壳。香不晓得手表是空心的,整天心里美滋滋的。香跟着老公沿街走来,几个小媳妇正聚在门口做针线活儿,有人叫住她:“香——几点钟了?”香终于开口了,她把手腕向内勾成直角,举起前臂,将手表向小媳妇眼前一亮,咬着舌头娇滴滴地说:“你自眙一眙哪。”小媳妇一看,放下针缝活儿,跺着脚说:“当死,差点儿忘了做饭,还好香有手表!”香咧嘴露出粉红的牙龈,像是全镇最幸福的女人,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后来经常有人问香几点钟,都会假装一惊一乍地表演,让香炫耀一番,也从来没人去戳穿。
最有能耐的讨饭人应该是昌某,他是我邻舍,是个讨饭头。他不必出去乞讨,镇上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送上红包;好脚好手的外乡讨饭人沦落到虹桥,也得向他“贡奉”,因而他家很少有缺吃的时候。青黄不接时,他家里还浸着两缸粿呢!记得他将粿分给邻舍小孩时,都会悄声说:“覅响,快拿去蒸起来吃。”有年端午节,他将一整袋的粽子都分给了邻舍。他在讨饭人中很有威严,可我们邻舍小孩并不怕他,趁他醉醺醺回来时,缠着他要钱,每次都将他兜里的铅角子掏光,让他老婆心疼得要死。
讨饭头的衣钵只能传给儿子,因而他老婆想教女儿唱道情,往后有门手艺好谋生。我见过一次她带上女儿唱道情,她拍打着道情筒,女儿跟着节拍唱。平时都一起玩的女孩,怎么突然变成了讨饭人,我觉得怪怪的,恍若是期末音乐考试,老师弹着风琴,学生跟着唱;女孩显然很不耐烦,眯眼看着围观的同龄人,又不断向屋里张望,希望屋里的主人快出来,终止这场无奈的尴尬,好让她回去跳橡皮筋。
讨饭头生个儿子时,各路讨饭人都来道喜。酒席从门口一直摆到晒谷坦,足有六十多桌,很多讨饭人都是第一次作为宾客坐到酒桌上,个个都吃得满嘴流油,喝到地摇月晃。这是他们自己的喜事——丐帮总算后继有人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虹桥街上已几乎见不到讨饭人。当年的讨饭头可曾想,子女会成长为成功的生意人,还成就了一番家业?又有谁还会惦记他的“讨饭生意”呢?也许,只有当年那些吃过他粽子的小孩儿,才会在端午节时还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