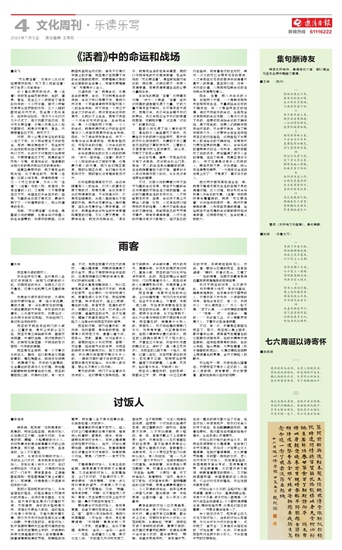雨客是外婆的同村人。
我与他并无交集,他只是我人生记忆中被随风一刮而飞过眼前的沙粒。我同雨客的关系,如同孔乙己之于鲁迅,仅是为他耗费几点笔墨的牵连。
我是在外婆家读初中的,外婆所住的村廓叫瑶岙,是一座千年古镇。镇的外围,有一条轮廓可见的城墙。外婆住镇西的天井坦,学校在城外的镇东。从外婆家到学校,我要经过一条长而多折的石板路,然后出城门,再过桥沿河到学校。
雨客的家就在将出城门的小街上,位置极佳,是我上学的必经之地。雨客家是三间临街平房,里面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透过破损的门板,依稀可见角落里一只破旧的老衣柜和一只床前的粪桶。
雨客是无业游民,是一个不事农务的主儿。据说,他以前是在戏班里做事的,唱拉弹都会。因游手好闲惯了,就懒得下地。家中的几亩薄田,也全靠他的老婆与儿女打理。而他整日醉眼眯眯地哼着他的戏腔。雨客的唱腔和二胡,我是听过的,有一定水准。不过,凭雨客那高不过五尺的身材,一幅尖嘴猴腮,两颗被烟熏黑了的大金牙,想必不是那种作生作旦的料。应是那种敲拉打鼓的伴演龙套,我们坊间叫后排人员。
雨客也算是穿鞋袜的人,所以扛锄挑粪之事,他是绝对不干的。就是农忙季节,他也要抖一抖河东吼狮之威,赶着老婆儿子去下地。而他却赖在家里,咪点老白干,翘上二郎腿,唱他的戏腔。或者变卖一些值钱的家什,到赌场上玩上几手,切点猪头肉过过瘾。偏偏雨客的运气,总不见得好,赌输了就拿老婆出气。所以,过路之人经常会听到雨客家的吵闹声。
雨客的对面,刚巧住着我的一房远亲。她叫香菊,是母亲的表姐。香菊是乡政府老文书,掌管公章大印。那年头,罚款、盖章、计划生育什么的,香菊的话比乡长还顶用。香菊一家住着一座体面气派的洋房,与雨客的破败平房成鲜明对比。因了这层缘由,我也偶尔到香菊家喝口水什么的,一提到对面吵闹不休的雨客家,香菊总是无奈地摇头。与这种人做邻居,想必也不是什么好滋味。
夏天的时候,城门下会坐着许多纳凉的人,他们要等太阳柔和些,再去下田耕作。点半钟光景,城外的河风,慢慢浮起,似无形的棉絮穿过城门,直奔小街。雨客的店门口也开始凉爽起来。此时,雨客的舞台会准时开场,门口聚集着好多人。那些纳凉的人也慢慢聚拢过来,我等赶着上学的学生,也经常停驻一会,看个热闹。
雨客穿着一件散开纽扣的中山装,上口袋里别着一支闪闪发光的钢笔。他坐于木条凳上,交着腿,支起一把二胡,开始有板有眼地自拉自唱。雨客的中山装,是不分酷暑秋冬的,即使汗流浃背,也不轻易脱下。他认为这是与种田农民不同的身份符号。雨客唱拉时,神情是十分投入的,旁若无人。我不知他唱的是哪门子戏,好像是京剧,反正是蛮好听的。在那个精神娱乐匮乏的年代,雨客的二胡确也擦亮了不少枯乏的心灵。尽管在三十年后,我在中秋月圆的韩江边上,谛听了一曲《春江花月夜》,与雨客的二胡不是一个档次。那是一位盲人在拉,发自树影婆娑的深处,悠悠漫于江面。那种萦绕的琴声,催湿了我的眼眶,人生事,花月夜,恰似春水东流,弦断何人诉?
雨客沉入唱腔中时,他的老婆一般都会立于一旁,咧着一口红红的暴突的牙床,笑呵呵地招呼观众。然后,看一眼低头拉唱的雨客,自言自语道:“嘿哟,你看这老头,又唱了……”她的神情,如同家中藏有某种古董而遮遮掩掩般的那种自豪。
我对于雨客的印象,也仅限于此。叫我要像小说家一样去刻画他,确是有难度的。他本是与我不搭界的人,只是我年少岁月中一个很奇特的符号,难免会有记忆。有一次,我问外公:“你认得雨客么?”外公一脸不屑:“怎不认得,一个贪吃懒做的赌棍……”“可是……哎……他蛮会……唱的……”我欲言又止。外公是勤劳忠厚之人,不喜欢这些油滑鼠辈。
不过,有一次,我算是正面碰见雨客了。那次,雨客刚从集上回来,散开着中山装,满身酒气地唱着他的戏腔朝我迎面走来。他的步履虽然有些踉跄,但走路速度是极快的。他低头走路,摇头晃脑,大声地唱着《杨子雄智取威虎山》,纵情恣肆地在田野上挥洒着他的豪情,全然不顾路人的眼光。
我让路于一旁,好奇地回头望着他。我想雨客不是什么正式的人,但此人很奇特,很有意思。我这样想着,直到他渐渐淡出我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