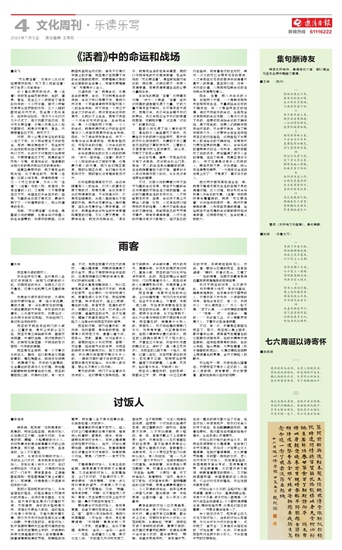“死也要活着”,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荒谬的吗?死了怎么可能活着?丢了命怎么还能保命?
这个看似荒谬的说法,是《活着》中的老全临死前讲的。当时,福贵、春生、老全三个人被困在了淮海战场中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对人民解放军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三个人随时都可能突然死去。老全是个老兵油子,他传授经验说:“老子大小也打过几十次仗了,每次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死也要活着。子弹从我身上什么地方都擦过,就是没伤着我。春生,只要想着自己不死,就死不了。”
然而,两个丝毫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活了下来,这个拼命想活下去的老全,却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老全的死比他说的那句话还要荒谬。他以前之所以不死,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侥幸而已。只要想着自己不死,就真的能不死吗?子弹,或者说命运,难道真的会因为你的想法而绕过你的身体吗?
但真正最荒谬的,既不是老全的那句话,也不是他的死,而是《活着》这部小说本身。讲得明明是一个又一个死亡的故事,为什么叫“活着”?《活着》中的人物,或者说,所有活着的人们,又有哪一个不是想着自己不死、希望自己长命百岁的?但是,残酷的命运却不肯放过,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叫福贵的老人,和头叫福贵的老牛。
无疑,“死也要活着”这句话,是整部小说的题眼,也是余华对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的一句悖谬的概括。这句概括所呈现给我们的,首先不仅是它字面上的矛盾,而且是它在捉摸不定的命运面前的荒谬。而要理解这样的命运面前的生命意义,则首先要理解“命”究竟是什么含义。
汉语中的“命”既是命运,也是生命的意思。命运,不过就是生命的走向。命运之所以捉摸不定,是因为并没有一个宇宙通德秩序来指引每个人的生命走向,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生命之外的命运;而没有在命运中的展开,也就谈不上生命,同样不存在一个与命运无关的生命。生命和命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个人的命运,就是或偶然或必然的生活环境与个人选择共同展开的生命走向。因此,为了保命而抗争命运,并不一定是与命运背道而驰,而是承担厄运,开拓好命的过程。人与命运的关系,更多像是一种游戏,而不是战争。
余华在提到他的这本小说的时候说:“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相互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
这句话概括得再好不过,命运伴随着每个人的生命,它对人的基本态度不是敌对,而是无情。命运本身不会依照道德标准,不会和谁妥协,它是完至随意的,会把人推向谁也不知道的方向,虽然会无意中给人造成痛苦,但也会无意中给人带来幸福。过日子,就是品尝命运所给的所有幸福和痛苦的过程。不论人愿不愿意,只要有命在,就无法逃脱命运,“混日子,就是完全消极地承受痛苦,同时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幸福。老全所说的“死也要活着”,是坚韧地面对命运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一定使人获得幸福,却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必要力量和条件。
余华如此概括“活着”这种基本处境:“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正是“过日子”的基本内容。
整部小说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死亡。春生的女人输血害死了有庆,风霞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而死,悲伤中的家珍也很快病死,风霞的丈夫二喜在干活时出了事故被夹死,二喜的儿子苦根竟然吃毛豆被撑死。到头来,只剩下了孤老头福贵。
命运总无情。福贵一家每当过日子有了点起色,厄运就会找上门来。每当一家人的生活其乐融融的时候,往往就隐藏着巨大的灾难。福贵似乎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战场,也永远没有结束他的赌博。
不过,这部小说的震撼力并不在于残酷的命运本身,而在于残酷的命运与幸福的家庭生活之间的碰撞。命运的残酷是生活的本来状态,人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是,命运并不是上天赐给人的唯一礼物。人还有他可以培养和改变的性情。人虽然不能取消命运的不确定性,却能用自己的气节寻求尊严,用爱来建造幸福。人对外在的环境没有多大影响力,但对自己的内在品质,却有着绝对的主动权。虽然一次次的死亡会带来无奈的悲凉,人之爱却在这无奈的悲凉中创造着只属于人的幸福。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内在价值,人用规则控制命运的活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活着,即人与命运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定规则并在规则中生活,尽量减轻命运中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涵养自己的性情,追逐尽可能好的命运。任由完全没有规则的命运支配,人是没办法活下去的:但要彻底消除命运的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把制定规则当成目的,只会疲于奔命。除了制定规则之外,人还要学会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格。这种品格不会帮助人取消命运的不确定性,本身却成为更加宝贵的财富。所以,余华见到的福贵虽然已经一无所有,阅历却都成了他的资本,使他懂得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活出了味道。而真正混日子的人,并不见得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人。哪怕家财万贯、子孙满堂,到头来活得毫无境界,“一大把年纪全活到狗身上去了”,才是混了一辈子日子的人。
把这两方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自强不息的造福过程。这个过程,就会形成余华所谓人与命运的友情。《活着》中的悖谬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死也要活着”这句话中的悖谬一样。既然死是早晚的事,人所可能获得的幸福,恰恰就在于在无情的命运面前悖谬地创造幸福。这种悖谬越大,生命的意义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