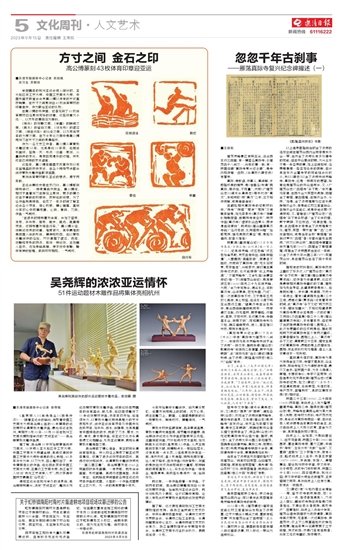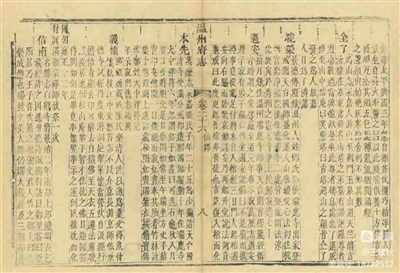
《乾隆温州府志》书影
■王建秋雁荡灵峰景区有鸣玉溪,沿溪西北行三四里,有一精蓝名真际寺,系雁荡古十八刹之一。近年修葺一新,有一民国旧碑“真际寺复兴纪念碑”,是寺内现存唯一古物,《乐清历代碑志选》有著录。
真际,佛教语,作真义、真谛解,亦即指成佛的境界,是《维摩经》所谓“同真际,等法性,不可量”。然而《广雁荡山志》《道光乐清县志》等书均作“真济”,未知何故?而“真济”二字,实不知作何解,或是谐音淆讹?
在翻检相关真际寺的记载材料中,“废寺”“废塔”“荒凉”“芜废”之词触目皆是。如元李孝光《真济寺》“绝巘松梯蹴翠盘,前朝废寺有空坛”、明项守祖《真济寺》“虚寂秋山古复今,荒凉漫诘旧禅林”、明何白《雁山重建真济寺疏》“经行老衲,礼废塔而兴嗟”“始感芜废,悟无常而达真空”等。是地处偏远,故香火难继?
明戴澳《重游雁山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卷一百三十二),记其游灵峰,过五老峰“对五老如逢夙昵,灵芝自烟中出,倒影照胆潭”,入碧霄院“洞壑故奇”,美景自不胜收。然而到了真际寺,因“无水石可赏,梵宇差洁”,兴味索然。原打算在真际寺过夜的,也只能悻悻“返上灵峰洞”,“夕宿灵峰寺”。又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游雁荡山后记》,载其崇祯五年(1632)四月二十九日游灵峰,大雨,“余乃赤足持伞,溯溪北上,将抵真济寺,山深雾黑,茫无所睹,乃还”。第一次游真际寺不成,又于是年五月初七再游,其心弥坚。他沿北斗洞下鸣玉溪西行三里,“望真济寺在溪北坞中,是溪西由断崖破峡而来……两旁逼仄石蹊,内无居民,棘茅塞路。行里许,甚艰,不可穷历。北过真济寺,寺僻居北谷,游屐不到”。可知真际寺所处之地,确实偏僻荒远,游人、香客难以穷历,荒废亦是自然。
《真际寺复兴纪念碑》(下简称《碑记》)中有“真际寺为雁荡十八刹之一,宋祥符元年与灵峰寺并创于全了法师”一段文字,据明朱谏《雁山志》载真际寺“宋祥符二年建置,熙宁元年赐额”,此“祥符元年”当系《碑记》撰者所误。全了法师,《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六“仙释”有传:
全了,永嘉人。(太平兴国元年)游荆门玉泉山,遇天竺僧,言:“汝缘在浙东,当得名山居之。永嘉有诺讵罗尊者道场,数适当兴,(宜往访寻,力成兹事。”了诘其所,答曰:“地以花名,山以鸟名,中有)龙湫宴坐,即尊者栖息处也。”二年归,至山下,问其村曰芙蓉,山曰雁荡,因感悟,即其地结芙蓉庵。雁荡之显,皆全了发之。为人放荡,人目为“了漭荡”。
括号中文字据《道光乐清县志》补,又《县志》“栖息”作“栖锡”。遍检各种《山志》,均无全了法师创建灵峰寺、真际寺的信息。又朱谏《雁山志》载灵峰寺“在东内谷,宋天圣元年僧文吉建,康定三年赐额”,明确记载开山者系僧文吉而非全了。而各种《山志》均无记载真际寺开山祖为谁。据府、县《志》,全了法师太平兴国二年归雁荡,若确是他创建灵峰、真际二寺,那要比朱《志》所载灵峰建寺早四十余年,真际建寺早十余年,事情确是如此吗?
当年全了法师在天竺僧的指引下来雁荡山,“问其村曰芙蓉,山曰雁荡,因感悟,即其地结芙蓉庵”,是所谓“鸟山花村”之处。而芙蓉庵者,明何白《汲古堂集》卷二十四“东洞记”有载:
有宋太平兴国间,禅僧全了经行至东洞,闻岩中童子诵经声,围绕作礼,竟于焉结刹,名芙蓉庵。后因高崖有飞来石罗汉,复名罗汉寺。
是芙蓉庵即罗汉寺也。罗汉寺在雁荡山西内谷,可以肯定此芙蓉庵非是灵峰寺或真际寺的前身。
2012年9月,《雁荡镇志》编写组在能仁村三官堂后山发现全了法师墓,位于大锦溪小锦溪之间,墓前有铭志镌“开发雁荡山全了祖师塔”(墓应系民国初雁荡山的开发者蒋叔南重修)。据村民介绍,建国前每年都有僧人到这里做法事,村人称这一带山为祖师坟山。
以上信息都指向当时全了法师的活动空间在雁荡山西内谷而非是东外谷一带。当然全了法师也有多处建寺的可能,但在开山草创时期,大兴土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空间地域、经费筹集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估计其在东外谷置寺宇的可能性会比较小。所以《碑志》以全了法师并创灵峰寺、真际寺,应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毕竟他是雁荡山的开山祖师爷。又,《广雁荡山志》“古塔寺”条下载:“宋天禧元年建。在西外谷大芙蓉长徼原,因僧全了骨塔,建古塔庵。在梯云谷外,今废。”如是,全了法师埋骨处应在长徼原梯云谷外,非是能仁村三官堂后山。自梯云谷外至能仁,或是中途迁葬?不得而知。又,曾唯在《广雁荡山志》“古塔寺”条下有条按语:“全了系宋初僧,熙宁赐额,不应称古。”说得在理。如是,此古塔寺亦非是全了法师埋骨之处。雁荡、芙蓉一带方言“骨”“古”二字发音相近,或是当年俗称“骨塔庵”后渐衍声为“古塔”者?与曾近堂先生同问,“识之以质山史”。据古塔寺建置在宋天禧元年(1017),因僧全了骨塔建庵,可推全了法师圆寂当在这一年前。以全了法师太平兴国二年(977)来雁荡山计,其在雁荡山生活了四十来年时间。
据现有的材料排比,真际寺历史上重修了好多次。《广雁荡山志》“真济寺”条下收录一篇文章《雁山建真济寺募缘疏》,记作者为宋虞淳熙,这应该是最早相关真际寺重修的文章。据张如元先生考证,此虞淳熙非是宋人,他是明钱塘人,字长孺,号德园,万历十一年进士,著有《虞德园先生集》二十三卷。遗憾这篇《募缘疏》没有署写作时间。此“真济寺”条下又记“明万历三十年,僧体如重兴”,不知这和虞淳熙为真际寺募缘会否是同一次的修葺?又何白《汲古堂集》卷二十八有《雁山重建真济寺疏》,亦未署年月,但记录了当时挂锡真际寺的僧人圆相上人,此次发愿重修的应该就是他。据此可知明万历间真际寺至少有两次重修,主事者僧体如、圆相二上人。“真济寺”条下又记:清康熙三十五年,僧定生再次修葺真际寺。遗憾的是上述僧体如、圆相、定生资料均无处稽查,诸上人生平事迹亦一无所知。
一直到清光绪初年,真际寺为某大族恃舍主之势,寺僧不堪其扰,山业渐废。而后寺址又为大道教徒所居,最终又舍去。至民国六年,为北斗洞道人兼理,亦屡致争讼,寺宇终至荒废。这些信息均见于蒋叔南《雁荡山志》对真际寺的记录。检之《碑记》“(真际寺)传至清咸同间,日渐衰落。光绪初年,寺产荡尽,宫墙坍坏”,其时实情可与蒋《志》相印证。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十四年(1935)两年里,有白波上人发大誓愿,重建灵峰、真际二寺。据蒋叔南《雁荡山志》载,灵峰寺在清同治间为某大族恶人所毁,取寺材为燃料,寺产荡然无存,其命运与真际寺同出一辙,估计此恶人或许便是当年真际寺的舍主。此次由白波上人大毅力修复,宫舍为之一新,其艰难曲折可以想见。
白波上人,俗姓李,大荆白箬岙人,出家观音洞。民国三十年(1941)后圆寂,墓在真际寺旁。墓穴三眼,中间书“净域”,左右分书“光前”“裕后”,又墓额“涅槃处”三个恭楷大字,旁有小注,略述白波上人生平。书者王梦曾(1873-1959),字肖岩,东阳人,清增廪生。曾任杭州府中学堂、宗文中学、女子师范、法政专门学校教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因日寇侵华,杭州沦陷,宗文中学部分师生迁徙雁荡,王梦曾随之而来。其与白波上人应有交集,故有此一段胜缘。
又《碑记》有“今地内居士徐缉旨……等,鉴于该寺前败原因,恐(白波)上人一去,继续者难得其人,乃与上人商议,嗣后该寺持住选择佛门贤者继任,不得任恶劣者把持,再坏寺产”。世事难料,白波上人去后十馀年,雁荡山诸寺院僧尼为政府遣散,真际寺再次荒废。笔者第一次过真际寺,房屋荡然,仅上下二层基础地坎依稀见其规模。唯当年复兴石碑茕茕孑立于田塍,独对斜阳。然佛门自有继起者,近年又见该寺重修,栋宇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