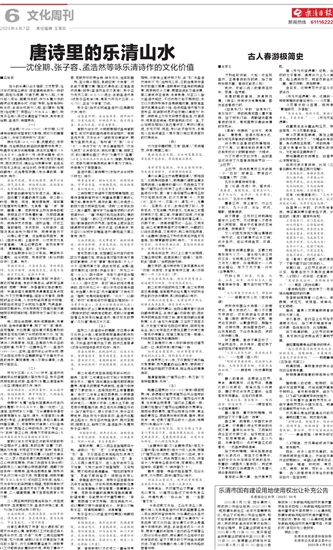如今的乐清以山水雄奇、文艺繁荣、经济发达而驰名遐迩。可在建县后很长一段时期,因地处海隅,交通不便,鲜为人知,少有外地人来乐。南朝刘宋时,作为永嘉太守的谢灵运来属县乐成“行田”考察,始有诗作吟咏乐成。此后乐成渐为人知。至《隋书·地理志》始记载了“芙蓉山”(即雁荡山)。唐代,则有多名诗人来过乐清且留下诗作,其中有沈佺期、孟浩然、诗僧贯休。
(一)
沈佺期(约656—714?)字云卿,以对律诗体制的定型有较大影响,而成为初唐著名诗人,与宋之问并称为“沈宋”。
神龙元年(公元705)春,武曌退位,中宗复辟。沈佺期因此前谄附武曌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与贪贿等罪,被流放至驩州(今越南荣市)。当年十一月,中宗受尊号,遂大赦天下,沈佺期虽因作为张易之党羽不得返京,而亦被放还,调任台州录事参军。他自流放地北上赴任,途经乐城,作有纪游诗《乐城白鹤寺》。这当是现存唐人咏乐清的第一首诗作。诗云:
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潮声应法鼓,雨气湿天香。树接前山暗,溪承瀑水凉。无言谪居远,清净得空王。
首联言白鹤寺地处东海之滨,高耸入云,且收藏了丰富的佛家经典。中二联从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等角度,细致真切地描写所见景物,尤其是“暗”“凉”等字,融情入景。尾联则承上抒发游寺的感触,表明自己不怨身遭贬谪,反而因得清净而入禅悟之境,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利得失。就诗作艺术而言,结构合理,对仗工整,音韵谐和,手法老到,允称佳作。但若与其此后所为相对照,则颇有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之嫌。沈佺期后来回京,竟以《回波乐词》上呈中宗,公然哀求为其升官晋爵:“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寡廉鲜耻,居然一至于斯。
在沈佺期游乐近二十年后,襄阳张子容遭贬,任乐城尉。张其时有《贬乐城尉日作》五律。诗云:
窜谪穷海边,川原近恶溪。有时闻虎啸,无夜不猿啼。地暖花长发,岩高日易低。故乡可忆处,遥指斗牛西。
首联点题,写身遭贬谪,来到“穷海边”,周边环境很差,有的只是恶溪。颔联写经常闻到“虎啸”“猿啼”,作者借写这样的景物,进一步渲染居处周围荒凉凄清甚至有点可怕,为下文抒情作铺垫。但在今天看来,倒是那时生态平衡,人与动物能共享自然环境。颈联出句写出了乐城地处温带,气候温暖,因而花期很长;对句则表现了因居处面对高岩而日照时间较短。尾联抒发了遥忆故乡的情感。
诗人因仕途困顿,身贬海隅僻县,失意侘傺,在诗中寄情于景,用了“穷”“恶”等字,自可理解,亦应同情。但毕竟对某些景物的描写客观地反映了乐城的可爱之处,如“地暖花长发”;另外,当时自然环境亦堪让虎、猿与人共同享有。况且,正是因为张子容的这回贬谪,引来了一位唐诗名家——孟浩然(689—740)。否则,孟浩然未必会来乐城,更不会因他与张子容唱酬而留下多篇关于乐邑的诗作。真可谓是:诗人不幸乐清幸,小邑而今益出名。
(二)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岁末,孟浩然远道前来乐城看望同乡挚友张子容。张子容闻讯特地前往迎接。孟浩然《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即是此时之作。诗云: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廨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乡关万馀里,失路一相悲。
诗题中“永嘉”当指包括属县乐成在内的永嘉郡(即今之温州市)。据《一统志》:“上浦馆,在府城东七十里。”又乐清青年学者郑向群君据永乐、隆庆、道光、光绪诸本《乐清县志》考证,上浦馆即象浦馆,其地今属乐清市磐石镇。又,郑君复针对通常人们以孟诗中“孤屿”即指江心屿的说法,作了考证,认为“孤屿”非江心屿,而是万家垟孤屿山(其地今属乐清市北白象镇张家湾村)。
首联以流水对写自己与前来迎接的张子容相会于上浦馆,其时已是“日暮”之时。 据此处所言,亦可证下文所言“孤屿”绝非江心屿。因相逢之际已是日暮,以当时交通条件,二人怎么可能来得及向西南跑几十里去江心屿游览题诗,然后又折回东北到乐城?颔联写二人遥对群山而把酒共酌,酒酣之际在孤屿一起题诗。孟诗当即是此篇,而张关于此行之诗今已不存,殊堪惋惜。颈联写廨宇(当指上浦驿馆)邻近瓯江与东海,当地人家与未开化的岛民隔水相望。尾联则是针对彼此的遭遇,孟浩然求仕不得,张子容宦海失意,二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地同有乡关之思。
二人同至县城时已是当年除夕,并且把酒守岁,且有唱和之作。孟浩然作诗二首,其一为《除夕乐城会张少府宅》:
云海访瓯闽,风涛泊岛滨。如何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余是乘桴客,君为失路人。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
这首五律表现了作者“他乡遇故知”的悲欢参半的心情。首联即以工对叙自己由水路来乐访友,且“云海”“风涛”二词见出境界开阔、笔力劲健。颔联以流水对谓在除夕得见故乡挚交,行文流暢而喜溢言外。颈联复以工对感慨彼此遭际的坎坷,表现了喜中之悲。尾联抒怀收束全诗,驹光匆匆,当年故里一别,至今异乡相见,其间已有“十馀春”,对此能不悲喜交集?据王达津选注《王维孟浩然选集》附录《孟浩然生平及其诗》,张子容为先天二年(公元713)进士,此前孟浩然有《送张子容赴举》诗,是年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正合“十馀春”之说。
张子容《除夜乐城逢孟浩然》应是酬和之作,诗云:
远客襄阳郡,来过海岸家。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东山行乐意,非是竞繁华。
首联为流水对,分明即是相对孟诗首联着笔,叙对方由故里远道来海滨相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颔联写设宴辞岁,更是为孟接风洗尘;“柏叶酒”之“柏”(谐音“百”)字与下句“九”字系借音相对,“灯发九枝花”系点染笔法,烘托欣喜之情。颈联工对,叙以善奏乐曲之“卢女”为高才之“孟嘉”(以史上同姓名士代指孟浩然)侑觞,用典贴切。尾联引谢安典表明此宴只是为了娱乐,并非是为了竞显奢华。
孟浩然第二首诗题为《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诗云:
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
二诗标题文字语序不同而题意相同。应是作者赋前首抒发久别重逢悲喜交集的心情之后,意有未尽,再作此篇。起二句追述从前因为世交而亲密无间。“续明”二句写此际二人异乡重聚,借守岁习俗催烛续明以彻夜把酒长谈。一“催”字贴切地见出其时心情的急切。“旧曲”一联以工对表现县尉府上辞岁筵以歌侑酒的热烈气氛。结尾承上摅发自己随遇而安的襟怀。 畅饮达旦,已是新岁。张子容以《乐城岁日赠孟浩然》酬和孟之第二首诗,诗云:
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插桃销瘴疠,移竹近阶墀。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
首句恐非泛言,包括辖区乐成在内的东瓯处于偏僻之地,而当含有对挚友款待不周的致歉意味。次句“建寅”是说新年(开元十四年)已是丙寅之年。由此句可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作品系年》 “开元二十年 (七三二)四十四岁 本年冬浩然自会稽经永嘉去乐城访张子容”,“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四十五岁 年初”离乐的说法是有误的,因为开元二十一年以干支纪年是癸酉年,与当事人张子容“风光肇建寅”之诗句不合。“插桃”句是说新贴春联(“桃符”)以辟邪,“移竹”句是说将竹移植至阶墀附近(竹为有节而虚心,历来以之喻高洁的人品)。颈联则是补述上二事虽是吴越风俗,却也是《荆楚岁时记》早就有记载的。尾联以东晋襄阳著名先贤来比喻孟浩然,是对好友的赞誉;“汉川湄”是说汉水之滨。
(三)
孟张二人此番在乐的唱酬,亦应是乐清文化史上令邑人感到荣幸而值得记载传扬的风雅之事。张子容安排孟浩然住在馆驿之中。不料孟浩然竟然生了病,因作五言排律《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作》。诗云:
异县天隅僻,孤帆海畔过。往来乡信断,留滞客情多。腊月闻雷震,东风感岁和。蛰虫惊户穴,巢鹊眄庭柯。徒对芳樽酒,其如伏枕何?归欤理舟楫,江海正无波。
起二句追述独自由海路来到乐城这一僻县。“往来”二句谓在乐收不到乡书而更加思念家乡。“腊月”四句谓在乐腊月即可闻到雷声,起春风时更感气候暖和;在洞穴中惊醒了冬眠的虫豸,在庭院的树上有着喜鹊巢。“徒对”二句承上言己因患病,纵使美酒当前也难以享受。依诗意来看,孟得病原因或许有二,一是思乡怀亲,二是水土不服。结尾表示要整理行装,乘江海风平浪静正好返乡。除了离家日久、思乡怀亲之外,张子容亦要赴京,因此开元十四年年初,孟浩然遂整装上路返乡。张子容送别孟浩然,同行至郡城,随即北上。临别之际,孟浩孟作《永嘉别张子容》诗云:
旧国余归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恋朋情。日夜故园意,汀洲春草生。何时一杯酒,重与季鹰倾?
首联点题,谓二人因各自登程即将分别。颔联以“愁”“恋”二字言别离之情:“愁”者,不仅因自己走海路忧愁波涛之险,而且亦有依依惜别的离愁;“恋”者,二人系同乡通家至交,在人生旅途中又各不如意,久别之后作了短暂相聚,又将别离,更不知何日再得重逢,“相见时难别亦难”,怎能不感到留恋?颈联出句写心情:,非唯孟浩然如此,即张子容在宦海浮沉中亦当难免;对句所写既是眼前所见景物,也当有暗喻乡思如春草一样萋萋生长之意。尾联将深重的离情别绪推向高潮:盼望有朝一日能更与对方重聚暢饮。“季鹰”即西晋文学家张翰,因见祸乱方兴,遂以蓴鲈之思为由辞官返乡。作者以之喻张子容,可谓用典精切,深具意蕴。
张子容亦以《送孟浩然归襄阳》诗酬和并送别好友:
东越相逢地,西亭送别津。风潮看解缆,云海去愁人。乡在桃林岸,山连枫树春。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第一首起联即以对仗写二人重逢旋复相别。次联承上言送别之愁,此“愁”与孟浩然诗中之“愁”当别无二致。三联当是写作者所怀故里之美景。结联是针对孟诗的明确答复,既表明怀乡之意,更显出彼此交谊深厚。第二首或作王维诗,未审孰是。反正二人皆为孟浩然知己,不过送别之地不同而已。本文以为即作张诗亦自是顺理成章。首联言孟浩然孤高绝俗的个性。他深知孟浩然难为浊世所容,故颔联诚恳劝他干脆以遁世为“长策”。颈联承上为好友设想家居生活,饮酒读书,何其自在逍遥。尾联言就此过这一生,不必如司马相如以自己著作求人赏识以谋仕进,亦无不可。而且,张以此劝告好友,亦是他入仕后深谙正人君子难以适应恶浊官场的切身体会。
(四)
大约在中唐时期,又有“回道人”来游雁荡,作有《题壁二绝》:
展旗邀我过天聪,玉女双鸾展笑容。卓笔蘸干龙鼻水,等闲题破石屏风。
昔时曾卧龙湫水,今日止兹续旧游。何处酒家堪醉月,兴酣解却白狐裘。
清代乐清名士方尚惠谓回道人“即纯阳也”,也就是说回道人,就是唐代道教全真派祖师吕岩。《全唐诗补编》551页吕岩名下亦据《广雁荡山志》收录了上述二首诗。现对作品进行分析。第一首七绝将雁荡山景观名称巧妙地联缀成诗,依次为展旗(峰)、天聪(洞)、玉女(峰)、双鸾(峰)、卓笔(峰)、龙鼻(洞)、石屏风(崖壁)。此诗运用了拟人、夸张手法,文笔流暢,气势非凡,尤其后二句堪称神来之笔。第二首,开篇追忆旧游,次句言此番来是重游。作为云游四海的著名道人,行踪不定,一游再游雁荡这一名山,又何足怪。后二句谓要寻酒家对月暢饮,兴酣时纵以白狐裘换酒,又有何妨。就二诗风格而言,与 《全唐诗》吕岩名下所收的其他作品亦无差异。如《题黄鹤楼石照》诗云:“黄鹤楼前吹笛时,白蘋红蓼满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
此诗流利空灵,与以上二首大体相同。又据各种记载,吕洞宾常以“回道人”自称。故此“回道人”当即吕岩无疑。
唐文宗时,温州刺史张又新来属县乐成“行田”与游览,亦留有诗作三首。其《行田诗》(一作《白石岩》)云:
白石岩前湖水春,湖边旧径有清尘。欲追谢守行田意,今古同忧是长人。
前二句写行田时所见之景。后二句表明自己是追踵、继承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关注民生的行迹与精神。其《游白鹤山》诗云:
白鹤山边秋复春,文君宅畔少风尘。欲驱五马寻真隐,谁是当时入竹人。
白鹤山即丹霞山,当因山麓有晋代古刹白鹤寺而得名。此诗系叠《行田诗》韵,因此写作时间当在行田之后。首句言白鹤山自晋张廌(文君)舍宅为寺至唐,又经历了四百多年。次句言文君旧宅因已成禅林,因而无有俗尘。后二句写自己亦想如王羲之访寻文君一样来访寻高士,可谁又是如文君一样避入竹林而拒见官员的真隐呢?
张又新是历代诗人中较早游览过雁荡山的一位,其时作有《常云峰》一诗:
仙府灵台莫漫登,彩云香雾昼常蒸。君能到此消尘虑,隐豹垂天亦为澄。
此诗寥寥二十八字,不仅展现了常云峰云蒸雾蔚、岚气氤氲的仙山景象,更表明了来此寻幽访胜时万虑俱消、超尘绝俗的高情逸致。
据清曾唯辑《广雁荡山志》,张又新“又有照胆潭诗,失传”。
(五)
晚唐名僧贯休(832—912)原有《诺讵那赞》诗,很遗憾这首赞颂雁荡山开山祖师的诗作今已失传,只留下残句:“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但仅此工整的一联,已真切地描绘了雁荡山仙境般的云雾缭绕、烟雨迷濛的景象。雁荡山现有经行峡、宴坐峰的景观名,即由贯休诗句而得。据传,贯休另有一诗,记载了雁荡山的十八古刹,诗题即为《咏雁山十八寺》:
本觉凌云到宝冠,能仁古塔上飞泉。普门罗汉石门里,瑞鹿华嚴天柱边。古洞灵峰真济并,灵巖霞嶂净名连。石梁不与双峰远,十八精蓝绕雁巅。
《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续拾》卷五十二据光绪《乐清县志》卷十六收入此诗。而据《广雁荡山志》记载,雁荡山十八古刹,有十七座建于宋代。则此诗显系后人伪托。作者将十八所佛寺名连缀成诗,可谓用心良苦。但诗中,将普明(寺)误作普门(寺)。
唐末,僧惟一寻幽访胜至雁荡,见山水奇秀,大为赞叹,因作《雁荡山》诗云:
四海名山皆过目,就中此景难图录。岩前逢个白头翁,自道一生看不足。
诗虽通俗,然对雁荡山之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以雁荡山胜过了域中所有名山,并借所遇一“白头翁”言,一生都“看不足”。
千年纪载文光灿,江山亦须名人扶。唐代诗人尤其是孟浩然这样的盛唐著名诗人来乐游历并留存诗作,为乐清的山水自然风光平添了人文光彩,丰富了乐清作为“千年古县”的文化内涵,在乐清文化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而且,此后自宋迄今一千多年,更有大量的包括诗人在内的各方面著名人物纷纷来乐游历,使乐清成为名驰中外的旅游目的地,留下了更多的文艺作品与游踪行迹,不能不说是唐代诗人起了导夫先路的显著作用。